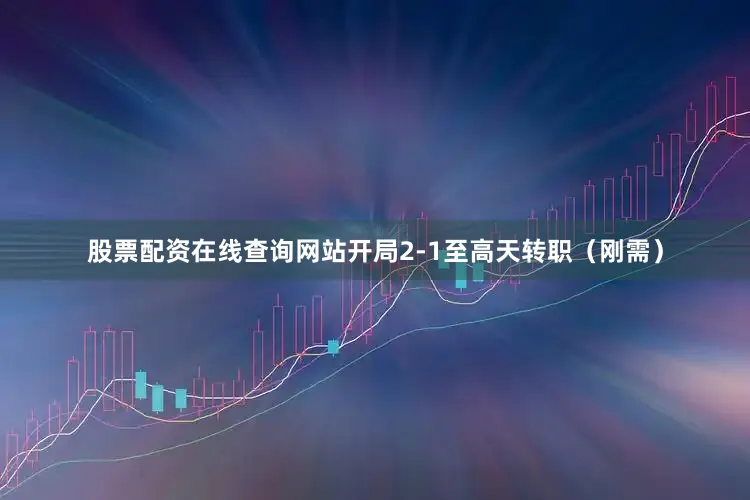图片
这条在《康平本》是顶格条文。其中有十来个字是旁注内容。
我们解读一下:
这条和前面的第40条没有本质的区别。但是这条在强调没有经过发汗,又现这个方证的,仍然属于本方的治疗范畴。这一点也挺重要。很多人在理解经方理论的时候,常把病因看的很重,认为古人说了这是发汗以后产生的症状,没经过发汗能治吗?这条等于给举了一个例子。从这儿再进一步地往深里想一下,在经方理论中影响治疗的关键因素不是病因。你看第40条和第41条就能看出来了,这两条论述的是一个病。一个是说经过发汗治疗以后,没有治疗如果也是这种表现的,还得用这个方子来治。实际上这个病因是帮助我们理解病理,区别这个疾病的性质,帮助我们辨证的,它有相当重要的作用,但是它对治疗影响不大。这一点是经方理论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。其他任何医学都在强调病因,传统中医里有“风寒暑湿燥火”等等,甚至都包括什么季节什么的那一大堆东西都罗列上。现代医学也是细菌、病毒,甚至有的卫生部的专家发现怎么着也躲避不了细菌的侵蚀,东西都不敢吃了,最后把自己给饿死了。所以经方的这些东西,你越深究、越去反复地玩味,就会觉得它所蕴含的道理就越深,而且价值越高。因为它是来自于实践的,它是正确的,你可以理解不了它,但可以逐渐地深入理解它。
“伤寒心下有水气”,刚才说了未经治疗,表现为“咳而微喘、发热”。实际上这些症状也不外乎第34条、第40条说的那些症状。
“不渴”是在这条里要强调的,应该有它的意思隐含在里面。首先“不渴”是这个方证的一个常见症状,所以作为一个典型的症状列在这个地方。临床当中,真正是小青龙汤证表现为口渴的非常少,最起码我没见过。有可能它有里热的话会口渴,那就不是小青龙汤证了,最差也是个小青龙加石膏证了。这是一个常见的症状,因为它有寒饮嘛,也印证了前面那个“口渴”在某种程度上除了停饮的因素,就是跟发汗可能有关。再一个意思就是强调既有停饮又没有里热,这一点也非常重要。一旦有里热,要么是大青龙汤证,要么是小青龙汤加石膏证,也应该包含着这个意思。
下面有一个旁注内容“服汤已渴者,此寒去欲解也”。这可能是这个旁注的作者临床当中一个经验,本来的意思就是说服了小青龙汤以后,这是有效的一个征象。实际在临床当中,小青龙汤证服了小青龙汤以后很少出现口渴的。因为它本身就有寒,把寒给它去了,没有寒了,也没有饮了,这时候人正常了,为什么会渴呀?这个很少出现。出现这种情况,恐怕本来应该是小青龙汤加石膏证,没有辨好证,该加石膏的没加,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,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比较大。这个地方在《宋本》上看不出是一个旁注内容,它跟正文是一样的,而且列在小青龙汤主治之前。从内容上看,它又跟原文明显地有不能接轨的地方。所以很多人都把它解释成是倒叙的一种方法,就是说倒插的。这就能看出把旁注内容篡入正文对读者的误导。如果任何一个人见到《康平本》的话,就再也不会这么解释了!所以也进一步地可以看到《康平本》的重要性。
这一条列举的症状很少,比较精练,或者说不太全面。但是按照读古人的书的正确方法来理解,实际上还有很多的症状已经包含在里面了。因为前面有“伤寒心下有水气”,“伤寒”就包括了一大堆的表实证的症状,像发热、恶寒,头痛,甚至包括身疼痛,这都完全可能出现的;“心下有水气”也不是说的一句白话,尽管是对病理的解释,但病理是以症状的形式反映出来的,它有“心下有水气”相应的一堆症状,这些症状在前面的或然证里都包括很多了,看看方剂也应该知道。
下面我们对这条作一个小结:阳性表实证同时又伴有停饮,其症状反应为咳而微喘,发热不渴的,为小青龙汤主治之证。
下面再看看方子。
图片
小青龙汤是个常用方剂,由8味药组成:麻黄、芍药、细辛、干姜、甘草、桂枝、五味子、半夏。麻黄、桂枝、芍药、甘草这四味药,我们可以把它们理解成小青龙汤的一个方规,或者说是小青龙汤的一个组方之一。如果把这四味药看成一个方子就很容易理解了,这药咱们前面都学过,无非就是桂枝汤里的主药和麻黄汤里的主药,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发汗解表,这是很明确的!另外像细辛、干姜、五味子、半夏,这些药也挺有意思,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温里祛饮,而且它们都有治疗喘和咳嗽的功能。可是治疗的却不是一种情况:像五味子和干姜,干姜也能治咳嗽,像理中汤还治因为里寒造成的咳喘这类的病,实际上主要还是干姜的功能;五味子也治咳嗽也祛饮,但是它们治的不是一类。其他的药也都有类似的特点,它们都治各自不同的原因造成的咳嗽。小青龙汤证的一个很重要的典型症状就是咳喘。为什么小青龙汤治咳喘这么好呢?就是因为它是从多方面的、大的方向就是温里祛水具体治咳嗽;前面的四味药它还有一个解表的功能,解表本身也能治咳嗽。所以说这个方剂在临床当中治咳喘的机会是比较多的。但是得有小青龙汤证,得符合小青龙汤的适应证,不符合是治不了,仅仅是盯在咳嗽上那也不行。
下边看方证:
症状(也就是说疾病反应症状):喘、咳嗽、咳痰、恶寒、发热、胸闷、干呕、下利、渴、小便不利、胸满(胸闷)、纳呆、水肿、周身乏力、流涕、头痛,这是主要的症状,还有若干症状因为出现的几率比较低,就没有统计。大家明显能感觉出来,小青龙汤所治的这些症状都比较繁杂,面也比较宽。
舌质:以淡舌、胖淡舌和紫暗舌。胖淡舌能体现出有停饮的一个特征。
舌苔:以白苔为最多,另外还有薄白、白滑、黄白润、黄腻。
脉象:脉象弦滑、弦紧、浮紧、浮滑、沉紧、沉弦、滑,就这么几种脉象。
现代应用看看小青龙汤治愈记录的现代疾病:流行性感冒、湿性胸膜炎、结核性或渗出性胸膜炎、大叶性肺炎、间质性肺炎、急慢性气管炎、支气管哮喘、喘息性支气管炎、肺结核、肺气肿、肺心病、百日咳、小儿手足口病(这个小儿手足口病是日本人的经验,那么是不是我们现在的手足口病有待证实)、急性腮腺炎、青光眼、结膜炎、泪囊炎、虹膜炎、慢性鼻炎、过敏性鼻炎、急慢性肾炎、肾病综合征水肿、荨麻疹。
下边我再跟大家说说我应用小青龙汤的医案,因为小青龙汤是一个应用机会比较高的方剂。说三个我的小医案,都有自己的特点,咱们从中体悟一下临床当中应用小青龙汤。
有一个医案是我同学的母亲,80多岁了。我同学打电话说他妈妈感冒了,先输了7天液,以前感冒输上7天差不多就好了,但这次没好,后来又输了7天还不好,就不敢再输了。这老太太的女婿是我们这儿医院里的一个主任医师,他知道抗生素的副作用相当大,也经常在家里边说,所以老太太就不敢再输了。就想着看中医,给我打电话说能不能去看看,我就去了。她有个很重要的特点:除了一大堆感冒症状以外,就是咳嗽,咳嗽的睡不着觉。很胖的一个老太太,她说晚上咳的都睡不着觉,越躺下咳嗽越厉害。大家注意啊,这个医案是以腹部停水为主要特点的。为什么啊?因为她到医院里边做胸透去检查了,肺部有很轻微的炎症,几乎都可以不称其为病,但她老咳嗽,连医院里都束手无策,不知道该怎么治。我经过辨证以后就给她小青龙汤。因为是熟人,再加上她年龄大,心脏也有点不好,小青龙汤里有那么多的麻黄,我晚上就在那儿坐了一会儿,等她服完药以后大概 一个多小时,没有明显的感觉,我就又让她服了一次,后来我就走了。到了第二天,我顺路去看她,她就说:“我昨夜到了下半夜(她第一次服药是晚上以后了),哎呦!我开始能睡觉了,今天午饭以后我又开始睡,睡了差不多大半个下午”。咳嗽也明显得轻了,而且她腿的水肿的皮肤开始变松了。第三天我去看她,一进门她就给我说:“冠杰啊!我该怎么谢谢你啊!你给我治好了这个病”。她说感冒咳嗽一点症状都没有了。后来根据她当时的情况,给她喝了一点别的药就好了,小青龙汤就喝了三天,六剂。这是一个医案。
另外一个好像说过。这个人每天早晨锻炼,不到 50 岁的样子,已经坚持了十好几年了,每天早晨要快走一个半小时多。他去年冬天就开始咳嗽,他的特点是晚上一点都不咳嗽,而且睡得很好,到白天就咳嗽得挺厉害。我经过辨证以后,他除了脉象有寸关沉细,迟脉,多少有一点浮象之外,其他的几乎没什么症状,像大小便、睡眠什么的都很正常,这就等于近乎无证可辨。我一开始就觉得是个小青龙汤证,但是他晚上一点也不咳嗽。我就问他:“你有没有手脚发凉的这种症状?”他说没有。我说:“我晚上回去的时候我把药给你带回去(也是住的离我很近)”。我就想给自己一个回旋余地,我再想一想。到了下午,他又托他的一个同学来给我送了一个信说:中午睡完觉以后发觉脚有点凉。我说好——小青龙汤合上麻黄附子细辛汤,实际上就是小青龙汤加一点附子,但是辨证思路是这样,他有一点阴证了。另外,我知道他每天活动,我曾经问他:“你走得这么快,有跑的情况吗”?他说:“我不能跑,我跑几步我心脏就受不了”。这是我用的依据。小青龙汤合麻黄附子细辛汤给他以后,越吃越轻,慢慢就好了。也没吃多少天,这经方治病本来就很快。
还有一个是我们小区里边的保卫,他以前是武警,现在60多岁了,体格很壮,每天早晨坚持锻炼。他说平时喝酒,酒量很大,喝白酒半斤以上没有问题,经常喝酒。他平时饭量还特别大,比别人高一倍。我以前跟他聊天心里就这么想,像这种人如果要发病的话,肯定离不开里热,因为他经常喝酒嘛!
有一次也是晨练走到一块了,他跟我说:“我这一段老咳嗽”。
我说:“你有感冒症状吗”?
他说:“有点流鼻涕,别的没有”。
我首先想到是麻杏石甘汤,就问他,出汗吗?
他说:“很少出汗,现在这段时间天热了有点出,但是没有正常人出汗多”。
这就是有点偏于表实证,这样跟麻杏石甘汤又不太对路。
我又问:“小便怎么样啊”?
他说:“不太好!老是量也小,次数也多”。
我说:“咱现在锻炼着也不能摸脉,吃完饭上班走的时候,我顺便再给你看一下”。
后来我就给他摸了脉,看了看舌。辨证如果一点资料没有,就凭着望诊,可以不带主观倾向,但是有了资料以后你肯定会有倾向了。我还是在找他到底是麻杏石甘汤,还是小青龙汤,后来一摸脉,脉偏迟、细弦、偏沉,就这一个脉就定死了,肯定是小青龙汤证了。我又看他舌淡暗、舌苔薄白,齐了。
后来我就给他说:“我中午给你捎药回来”。我中午让他服了小青龙汤一次、大概不到 4 克的样子,后边就改成2克多,服了两天。
第一天他服完了以后说:“中午吃了以后我出了些汗,还是有点咳嗽”。
我说:“你感觉轻松点吗”?
他说:“轻松多了”!
后边就一直这么服,前后总共服了五六天就全好了。因为他年龄稍大一点,给他控制的药量小一些。
这三个病人虽然基本上是一个方证,但各有侧重啊。一个是腹部停饮为主的;一个是肺部停饮的,机能还偏于不足,小青龙汤合上麻黄附子细辛汤;另一个就是这个警卫啊,他既有表证又有停饮,各占一半,而且他没有躺下以后咳嗽得厉害这种倾向。
所以这就印证了条文里边列的那么多或然证,这一类的方剂,它表现的症状不是那么单纯,相对说比较复杂,面也比较宽,它有这样的特点,这个方剂中把它论述出来了。可是在理解这个条文的时候,那就不是这样了,方后加减就出现了很多的,一旦见到或然证就加减,一加减就要出问题。因为对方后加减的理解,直接可以反映你对经方理论理解的准确不准确的问题。
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匮要略》都存在这样的问题:凡是条文里有或然证的方证条文,在方剂的后边都有相应的加减,跟条文里的或然证是一一对应的。作者的意思,出现某种或然证,就应该作相应的加减。只有理中丸这个方剂除外,因为理中丸这个条文里没有或然证,但是后边也有方后加减,等学到的时候我们再具体地分析。其他的条文都跟小青龙汤证的方后加减是相同性质的问题,尽管具体的药味不一样,加减的方法不一样,但是性质是相同的。小青龙汤条文是本书第一次出现方后加减,相同的问题我们还会放到后边适当的时候讲,比如小柴胡汤,我们在分析方后加减的时候再讲一部分。
图片
第一个问题,关于方后加减我们应该怎么认识。小青龙汤从整体来看,方后加减纯属无中生有。它就是作者在没有弄懂经方理论的情况下所做的“添足”之笔。为什么呢?我们具体地分析一下:先说条文里列举的所有或然证都是小青龙汤的治疗范畴,小青龙汤本身就可以治疗这些证,特别那个小便不利这是最明显的,小青龙汤里这么多祛水的药,可以非常好地治疗因里虚寒造成的小便不利,或者说小便不利造成的停饮也可以。实际上原来作者的本意就是想说,因为这个方剂它治疗的是既有表证又有停饮,又偏于里虚寒。特别是停饮这个问题是怪证百出,所以在这里特意给举了几个例子,这些都是在临床当中积累起来的。上次已经说了,像这样的方剂这么多的或然证,绝对不是一时一世总结出来的,这得是在若干患者身上逐渐地积累起来的经验。比如这个患者有咳嗽,那个有小便不利,另外的甚至发了汗以后还会出现口渴,就这样一点一点地积累起来的。作者也考虑到了凡有停饮证往往症状都比较复杂,而且这个方剂在《伤寒论》里相对排的次序又比较靠前,它处在基础的位置上,所以在这儿就交代得比较清楚。但是它总的意思就是出现这些或然证,都是小青龙汤的主治之证。
另外一层意思是经方的加减。经方不是不讲究加减,而且经方的加减出现频率还是相当高的,但经方的加减不是以这种方后加减的方式出现的。你看经方的加减:像桂枝加桂汤、桂枝去芍药汤,四逆加人参汤、四逆加茯苓汤、茯苓四逆汤,它不是以方后加减的形式出现的。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:任何一个经方一旦加减之后,它的方剂的适应证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比如桂枝加桂汤,没有加味,只是一味药变了剂量。所以说经方里所有的方剂都是非常严谨的,这是一套非常严谨的体系,而不是说经方的方剂不能加减,不是这个意思。它不是以方后加减的形式进行加减,从来不示范这么去作加减,而且条文本身也不是那个意思。
最后一个,方后加减好多看似有一些道理,但如果仔细地分析一下,每一个方后加减都有不合理的地方,跟经方理论接不了轨,这也能从侧面证明方后加减肯定不是出自经方原作者之手。而且从小青龙汤方后加减能看到,宋代的医书校正局的林亿他们看出了这一类的问题,后来加了一些暗语,也提出质疑。实际上历代都有质疑的,但总地说方后加减对后世的误导总是少数人,林亿他们的暗语就认识到了这一层,说这些或然证都是小青龙汤所主之证。但是到了小柴胡汤、四逆散、真武汤的时候,他又不这么认识了,这就是出专著的专家们太机械了,如果按他们的观点的话,林亿应该在每一个方后加减后面都应该写一个按语,他们觉得心里也就踏实了。咱们学习东西不应该这样,应该实事求是,我们应该学习胡老的精神。另外,既然我们把方后加减的性质给定下来了,方后加减尽管史料不多,但我们从蛛丝马迹里也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依据。首先,《康平本》和《宋本》都有方后加减,《康平本》又早于《宋本》,所以说方后加减应该在《宋本》之前,理论上说它也应该在《康平本》之前,至少是和《康平本》同一个时期加上的。要是这样的话,据我们所知只有两个人:一个是张仲景,一个是王叔和。张仲景是得到了《汤液经》,后来又作了一些补充,形成了《伤寒论》;后来王叔和找到了这本书,后面大家都知道了。这个内容肯定不会是《汤液经》的作者加的,只有张仲景和王叔和这两个人。用这种推理,再看看林亿他们的按语,《康平本》就没有,从这儿就能证明,《康平本》成书的时候,林亿他们还没有见到。
另外一种,我再跟大家罗列一下,《康平本》里“若渴者”成了“若渴”;《康平本》里“若喘者”在《宋本》里是“若喘”,没有“者”;还有一个小差别就是《康平本》里的“若嘻者”, 到了《宋本》里成了“若噎者”,这个就差了太多,不知道在哪一个环节出错了,显然是抄错了。条文里就应该是噎,原稿如果模糊,容易抄错。
这个方后加减就是出在王叔和之手。理由就是《康平本》和《宋本》之间的方后加减就这么一点文字,出现了好几处的不同之处,仔细看看,明显是经过修改的,除了“嘻”字之外,其他的明显都是经过修改的。只有王叔和有修改的可能性,因为通过两个版本的比较,我们发现凡是见到这个版本的人都非常慎重,甚至王叔和最初的时候,把原书的缺字都用方框给标记出来。古代抄写东西是往竹简上抄,一条竹简上几个字是有数的,漏字的情况非常少,所以这肯定是人为的修改的。特别像加杏仁半升后边又加了三个字,以前的书没有,这是特别明显的修改感觉。《康平本》以后凡是正规的版本,特别是《宋本》,宋代校正医书局校正的时候也特别严谨,他们也不会做这么大幅度的修改,只有一种可能性是王叔和改的,因为这本身就是王叔和自己写的,他在第二次整理的时候,他觉得改一下比较符合他的意思,会比较好一些。这也就印证了方后加减只能出自王叔和之手。方后加减本身从方向上、根本上错了,一是原文作者不是这个意思,另外那些或然症本身就是这个方剂能治的。
因为中药它有这样的特性:比如常见的发汗药像麻黄、桂枝,生姜也能发汗,甚至桑菊饮里的薄荷也能发汗,好多药性是比较接近的,但只是这一个点上接近。经方要这么加减了以后,方剂就不再是以前的方子了,它的适应症也会相应的发生比较大的变化。所以说这种加减一个是方向上有了错误,另外一个就是当到了《宋本》的时候,它跟正文完全没有区别了,就对后世理解经方理论发生了非常严重的误导。而且越是看的有道理,它的误导就越深。咱们现在随症加减这是一个比较深刻的问题,咱们以后再讨论。这个方后加减对后世理解经方理论产生了极大的误导,我现在就常用这个来界定一个经方学者,有没有真正把经方理论弄懂弄通,这是一个分水岭。能够看清这些方后加减实质的,一般经方应用水平就比较高,理解得也比较准确。反之那就可想而知了。
我想从实际临床的角度谈一谈,再给大家加深一点印象。前两天我这有一个病人,60岁左右的一个老太太,她主诉就是肠胃不好,心下痞,老觉得胃里不舒服,肠鸣,吃了东西以后老觉得肚子里咕噜咕噜的响,有时候下利,不是说老在下利。大家一听就知道差不多是一个半夏泻心汤证,比较明显了;同时还有脉迟涩,脉迟的严重,一分钟 50 多次;再一个是两脚怕冷,就在夏天她还觉得有点喜热不喜冷,精神不好,老想躺着;而且她还有一个特点,她是农村的,她来她姑娘这一天都待不了,她说我待这就觉得心里边支撑不了。因为她就是体质太弱,就是说心气不足,她觉得在自己家里环境也熟悉,心里也放松,想什么时候躺一躺就躺一躺,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我给她的方剂特别简单,半夏泻心汤合上四逆汤。看看这些药,换一种说法就等于说半夏泻心汤加附子,我在病历上写的却是半夏泻心汤合四逆汤。我们从这个医案试着分析一下,如果把它理解成半夏泻心汤加附子会是一个什么情况。要理解成是加附子,就具体到这个病人,就成了她的脉迟涩,脚恶寒,精神不好等等的都是附子证了,这成了附子主证了。如果按照半夏泻心汤合上四逆汤这种理念去理解,半夏泻心汤证还可以出得多一些,比如出现想呕吐也可以。这里还有一个事,她还有寒热错杂的情况,她脉跳的那么迟,她自己说我有点上火,牙龈还有点肿,这不是寒热错杂吗?特别符合半夏泻心汤证;同时她还可能出现更多的四逆汤证。所以说我们在辨证过程当中,我碰到的这个病人,她具体就这几个证,她再有四逆汤的其他的证可不可以?完全可以。你要理解成半夏泻心汤加附子的话,就等于所有的四逆汤证都成了附子证了。这就是理论上差之毫厘,临床当中就谬之万里。要那样的话,你在临床辨证过程当中,附子动不动就用啊,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合四逆汤啊,这种情况都会出现的。要如果在别的方证里边再出来,比如小柴胡汤又有嗜卧,你看见嗜卧这不是附子证嘛!你用小柴胡汤加附子,就没有道理了,那本身就是小柴胡汤治疗的范畴,没必要加附子的。如果这样推下去以后,大家会发现,一开始的时候看着还模棱两可,但是要是一跟临床去接轨,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,是一个原则问题。
另外,前两天我听到一种很普遍的说法。说经方也是由一味药一味药的这么罗列起来的,都是单味药相加,甚至经方里边有好几个方子就一味药嘛,像甘草汤,一味瓜蒂散啊。说这种观点的人,貌似特别睿智,特别有见地,而且还特别有气魄,大有他这一生足以和张仲景抗衡的这么一种气魄。但是这种观点对我们应用经方很不利。首先经方里的每一个方剂,都是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确定下来的最佳组合。这个没有必要多说了,有的用现代医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方,做了好多试验,到最后惊讶地发现,在两三千年以前中国古人搞的那些方子,它治疗相应的适应症的时候,只有它原配比组合疗效最好。实际上这本身就说明,它是经过了长期的临床实践,最终确定的一个最佳组合方案;另外,整体地看一看经方里所有的方剂,每一个方剂都是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筛选出来的最佳方剂;还有一个方面,就是经方里的每一个方剂,都对应着一种人体的典型病理状态。仔细分析一下就行,除了它举的个别的例子以外,包括它一些很偏僻的方子,那肯定是出现的那种证少,但是一旦碰到那种病人,你离了那个方子就解决不了。
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说,随证加减也是在不断的积累中,随证加减跟经方走的是两条路。在经方之前早就有随证加减的积累,不然王叔和不会搞了这么成熟的一套方后加减。这就是说,方后加减在王叔和之前若干年,甚至几百年、上千年早就有这样的一个医学派别,甚至它就是中医的一个主流,一直在积累,到现在始终没中断过积累,现在市面上的中医们大部分都在走这条路,而且积累的方剂成熟的也很多。《方剂大词典》里有一万五千八百多个方子,但这些方子却不足以和仅仅只有两百多个方子的经方抗衡,它没法相比。不是说那些方子不治病,也治病,它积累了这么长的时间,这么多人去积累,甚至后来派生出了很多的派别,像温病派、火神派、脾胃派啊等等。但没有哪一个派别超过经方的。这些随证加减积累起来的方子,从整体上离经方的境界差很远,而且很难找到有成熟的定型的方子,可以和经方里的单个方子相比。比如小柴胡汤,你很难找到一个能治类似病的时方,疗效和小柴胡汤不要说相接近,能有个差不多,有这样的方子那就不简单了。
所以,中医里很多这样的东西,要是初看感觉这个观点特别好,特别有价值,但要仔细地去分析分析就会发现有差距。具体到这个问题我们没必要舍近求远。古人已经给我们找到了最近的路,最合理的方剂组合,你再绕开它干嘛呢?无非就是下一点功夫把它学会了,学会了怎么用不就行了嘛!就是说没必要去舍近求远,应该下功夫把经方的理论学好。
再反过来看,那些随证加减积累的方子也都是一些好方子,也治病,用对了有些方子也是非常好的,也很有价值。如果能在弄通了经方理论的基础上再去看、去用这些方剂,那就会如虎添翼。我们看看胡老这一生的实践,就是说你要是能把经方学好了,你完全可以去做更深的探索,不做你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医生。关于方后加减就说这么多,等以后再碰到这类条文我们再深入地讨论。
小青龙汤里还有具体的一味药,就是细辛。为什么在这提出细辛来啊?细辛地临床应用中,据统计资料看,应用细辛的量最大的记录是40克,一剂药里边40克,而且患者服了以后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。在统计资料里有这么一个医案,医生给一个患者开的小青龙汤里边有 9克的细辛,吃了以后出现了呼吸困难,然后到医院经过抢救才脱了险。这就有一个问题,我们不能轻易地说细辛临床中大量用绝对没问题,但是更不能轻易地细辛不过钱,用这个给束缚住,你真的不敢用,应该还是小心一点好,因为实际临床中确实有这样的医案。如果讨论,我们不妨换一换角度思考一下,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?有的人喝40克没问题(还有人写过一本书,书名叫《细辛的临床应用》,作者曾经用水煮60克细辛喝了没事,比这个量还要大),但是临床中又确确实实有不到10克就出问题了。所以历史上这个“细辛不过钱”也不是空穴来风。但是这个结论下得过于得粗浅。
从我这个角度来看,我认为事情的实质应该是这样。按现代医学的解释,应该有的人对细辛这种东西过敏。咱们今天不应该讨论过敏的,过敏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病,治好了它就不过敏了。现代医学不知道过敏的原因是什么,如果遇到什么东西过敏了,它就让你离开这个东西,千万不要去接触它,实际上这都是被动的,把它治好了就不过敏了。所谓的过敏体质是因为治不了的病,给人家扣的帽子。这个地方就是说之所以用一点细辛就受不了了,是因为对细辛过敏,按现代医学和说法,这样好理解。为什么过敏呢?肯定在临床中有某些小青龙汤证之外的特殊症状反应,或者说是对小青龙汤证的某种反应比较强烈吧,但是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积累这样的经验。历史上就有人武断地说“辛不过钱”,不能大量用,大量用就坏了。现在临床实践中看有的人确实不能多用,但是大部分人多用了没问题,至少用经方的原量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应该去想这个问题,为什么?我的观点就是有的人过敏,他必定在临床中有相应的症状反应,肯定有特殊的证,但是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根源。临床当中可以去注意一下,总有一天能找到细辛使用的规律。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,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,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,请点击举报。
股票配资专业平台,专业的正规实盘配资网站,配资知名股票配资渠道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